近年来,随着区块链领域尤其是加密行业的发展,一些法律风险问题逐渐凸显。其中,职务侵占罪在该行业的适用性备受关注。
一方面,实践中已出现加密行业从业者可能涉嫌职务侵占犯罪的咨询案例,这使得探讨此罪在加密行业的适用情形颇具必要性。另一方面,从币安、欧意等大所的动作来看,行业内部对于腐败的打击力度呈增强趋势,这也凸显出梳理相关法律风险、推动合规建设的紧迫性。
本文将围绕职务侵占罪在加密行业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入分析。首先剖析该罪在加密行业适用时面临的诸如主体认定、行为界定等争议点;接着探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之可能产生的复合风险;最后对行业合规建设及司法层面的发展进行展望,以期为加密行业从业者明晰法律边界,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职务侵占罪的刑法构成要件解析
1. 犯罪主体认定标准
依据我国《刑法》,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明确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加密行业情境下,对于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境外公司(如虚拟货币交易所)及其在国内的分支机构、实控公司等能否构成该罪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存在认定探讨。经核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司法案例指出,即便公司业务涉及虚拟货币存在合法性争议,也不影响对员工职务侵占等犯罪行为依据事实与法律进行评价。此外,证明员工身份在加密行业有其特殊性,不仅可从有无签订《劳动合同》、缴纳五险一金等形式判断,更关键的是看公司对员工有无管理、支配及给付劳动报酬等职能。
2. 客观行为构成要素
从《刑法》规定来看,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在加密行业,若员工利用其在虚拟货币交易所或其他加密公司的职务便利,侵占属于公司的主流虚拟货币(如USDT、ETH、BTC等),鉴于其财产属性已获司法理论与实务共识,认定构罪争议相对较小。但若是侵占公司自己发行的代币,或者未来的预期利益(如未解锁、上市的代币),则在实务中构成职务侵占罪与否存在较大争议。
3. 量刑标准与立案门槛
我国《刑法》针对职务侵占罪设定了三档刑期:一般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同时,根据2022年最新司法解释,职务侵占犯罪的立案标准为3万元,此门槛相对较低,意味着一旦涉及相关侵占行为达到该数额标准,便可能触发刑事立案程序。
4. 司法解释的适用边界
在加密行业的司法实践中,司法解释的适用需结合行业特点审慎考量。例如,对于涉及虚拟货币相关财物侵占的案件,虽主流虚拟货币财产属性有一定共识,但对于一些特殊虚拟货币资产形态(如公司自制代币、未来预期利益相关代币)在适用司法解释时,需权衡其是否完全契合既有解释框架,以准确判定行为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以及如何适用相应量刑标准等,避免因行业特殊性导致的司法判定偏差。
加密行业特殊法律环境分析
1. 政策演变与监管框架梳理
自2017年「9.4公告」发布后,内地叫停虚拟货币融资项目,部分虚拟货币交易所迁出中国。2021年「9.24通知」进一步明确,内地所有与虚拟货币相关经营活动被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虚拟货币交易所在内地失去合规运营依据,纷纷迁至海外。同时,涉虚拟货币的多种业务活动如兑换等在内地也被禁止,相对安全的加密创业多为不涉及发币的区块链项目、虚拟货币钱包公司等。但「9.24通知」虽禁止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向内地居民提供服务,仍有不少内地用户使用境外交易所,且部分内地城市存在其技术、客服团队。
2. 境内外交易所运营模式差异
境内由于政策限制,虚拟货币相关经营活动被禁,已不存在合规运营的虚拟货币交易所。而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运营模式多样,部分以华人背景成立的交易所吸引了大量内地用户。在劳动用工方面,境外交易所或其他加密行业公司在内地可能通过劳务公司等「中介机构」或实控公司雇佣员工,甚至存在不签劳动合同、以代币发放工资的「洒脱」web3用工模式,与境内传统用工及运营模式存在显著差异。
3. 非法金融活动认定标准
依据相关政策,在内地,虚拟货币发行融资、虚拟货币与法币及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定价和信息中介等业务活动均被认定为非法金融活动。其认定主要基于维护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等考量,以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4. 司法实践中的法益保护逻辑
在司法实践中,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官方账号相关文章所表明的观点,即便涉及虚拟货币业务的公司其业务在内地可能存在合法性争议,但员工若存在职务侵占等犯罪行为,仍会依据查明的事实及相应法律规定予以法律评价。这体现了司法实践中对法益保护的逻辑,即不因业务本身的合法性争议而忽视对犯罪行为的惩处,旨在维护公平正义以及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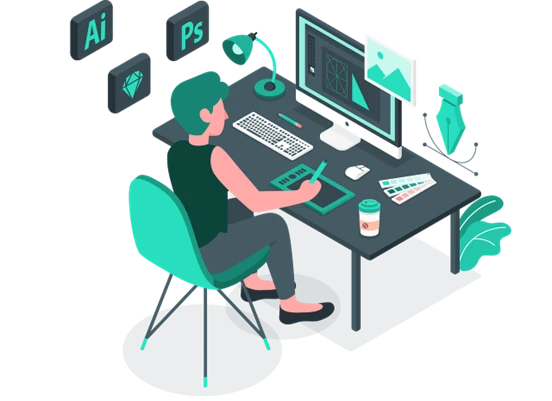
职务侵占罪在加密行业的适用争议
1. 非法主体的司法认定标准
在加密行业,职务侵占罪涉及的主体认定存在复杂性。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通常应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然而,对于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境外公司,如虚拟货币交易所,及其在国内的分支机构、实控公司等能否构成该罪所指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存在争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官方账号曾表明,在虚拟货币交易所业务场景中,即便交易所自身业务在内地合法与否存疑,若员工存在职务侵占等犯罪行为,仍会依据查明的事实及相应法律规定对其行为予以法律评价。这意味着,司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因公司业务的合法性问题而简单排除对相关主体的犯罪认定考量,但具体认定标准仍需在各类案件中进一步明晰。
2. 劳动关系的特殊证明方式
证明加密行业从业者与公司的劳动关系也颇具特殊性。从表面看,可依据有无签订《劳动合同》、缴纳五险一金等来初步判断。但在加密行业,情况更为复杂。例如,虚拟货币交易所或其他加密行业公司,在现实操作中多不会直接以自己名义在内地雇佣员工,可能会借助劳务公司等“中介机构”或其他实控公司(在内地并不经营涉币类业务)作为劳动用工主体。甚至还存在更“洒脱”的web3用工模式,即不签订任何劳动合同,直接以USDT或其他代币发放工资。在此情形下,确定职务侵占罪的被害人身份在实务中便争议颇大,无论是控告方还是辩护方,都需运用各种方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如何准确证明劳动关系成为关键难点。
3. 虚拟货币财产属性争议
当涉案资金、财物为虚拟货币时,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也存在争议。就主流虚拟货币如USDT、ETH、BTC等而言,利用职务便利侵占这些属于公司的虚拟货币构罪在实务中争议相对较小,因为其具有财产属性已在司法理论和实务上达成共识。但若是侵占公司自己发行的代币,或者是侵占某种未来的预期利益(比如还未解锁、上市的代币),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则争议。这些情况涉及到对虚拟货币财产属性更深入的界定以及对职务侵占罪构成要件在加密行业特殊情境下的理解与适用,亟待进一步探讨与明确。
4. 自建代币与预期利益认定难点
在加密行业,自建代币及预期利益的认定是职务侵占罪适用中的又一难点。对于公司自己发行的代币,其价值评估、所有权归属以及在职务侵占情境下的法律定性都较为模糊。比如,如何确定侵占公司自建代币的具体数额以及该行为对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等问题,都缺乏明确的标准和统一的司法认知。同样,对于侵占某种未来的预期利益,如尚未解锁、上市的代币所对应的潜在收益,其认定更是困难重重。这不仅涉及到对虚拟货币市场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考量,还关系到如何在法律层面准确衡量这类特殊“财物”在职务侵占罪中的地位与性质,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严峻挑战。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复合风险
1. 受贿与职务侵占的竞合情形
在区块链领域的加密行业中,部分从业者可能面临受贿与职务侵占竞合的法律风险。以实际案例来看,经核查存在“石某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石某玉利用职务便利,一方面在引进合作业务(虚拟货币奖励)时非法收受其他公司财物,另一方面又通过公司账号将虚拟货币变现后据为己有。在此类情形下,从业者的同一行为可能同时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出现两罪竞合的状况。
2. 典型案例司法裁判逻辑
从上述典型案例的司法裁判结果可知,法院会依据查明的事实及相应法律规定,对被告人的行为进行全面法律评价。即便案件涉及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其业务性质是否合法并不影响对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认定。就像石某玉案,最终被法院判决同时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并给予数罪并罚的惩处,这体现了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复合犯罪行为秉持严格依法裁判的逻辑。
3. 数罪并罚的量刑影响
当从业者出现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职务侵占罪竞合并被判定数罪并罚时,量刑会受到显著影响。如石某玉最终被执行有期徒刑12年,相较于单独构成其中一罪,数罪并罚的刑罚力度明显更重,这彰显了法律对于此类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态度,以起到更强的威慑作用,维护行业的正常秩序。
4. 跨境司法协作新趋势
随着加密行业的全球化发展,跨境司法协作在处理涉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相关案件时呈现出新趋势。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区块链及虚拟货币的监管政策存在差异,但在打击跨境犯罪方面的合作逐渐加强。比如,对于涉及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员工的犯罪行为,国内司法机关可能会与境外相关机构进行协作,通过调证等方式获取证据,以确保对犯罪行为的准确认定和公正裁判,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行业合规建设与司法展望
1. 大所内部反腐机制升级
从币安、欧意等大型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公开举措来看,未来针对内部腐败的打击力度呈现出不断强化的态势。鉴于加密行业中中心化机构在过往监管相对宽松,诸如内幕交易、从业者与做市商及项目方勾结等不良现象屡见不鲜,而这些违规行为的违法成本偏低且查处难度较大。在此背景下,大所加强内部反腐机制建设,有助于规范行业秩序,提升自身运营的合规性与稳健性。
2. 跨境监管合规压力传导
随着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web3产业的合规监管日益趋严,加密行业面临着跨境监管合规压力的传导。不同地区监管政策的差异,使得加密货币交易所及相关从业者需在全球范围内协调自身业务,以满足各地监管要求。例如,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虽在部分地区运营,但需应对内地关于禁止向内地居民提供服务等政策限制,这就要求其在跨境业务开展中更加注重合规操作,避免违规风险。
3. 法律实务辩护空间分析
在涉币类职务侵占犯罪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等法律场景中,站在辩护律师的角度,存在一定的辩护空间。一方面,由于加密行业用工模式多样,如采用劳务公司、实控公司作为用工主体或web3特色的用工方式,使得确定职务侵占罪的被害人身份等环节在实务中颇具争议。另一方面,对于侵占公司自发行代币或未来预期利益等情况,在是否构成犯罪的判定上也存在较大争议,这些都为专业的web3律师提供了在辩护时可据理力争的要点。
4. 行业合规化演进路径
综合来看,加密行业的合规化演进路径正逐渐明晰。受大所内部反腐加强及跨境监管趋严等因素影响,加密货币交易所及其他加密行业的内部合规发展有望与传统互联网公司不断趋同甚至实现进一步进化。
